相聚思想云端 探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暑期系列讲座实录
2020年8月8-17日,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在线举办了“中国文化暑期系列讲座”,邀请了校内外10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典籍、经典诗词、传统思想、艺术文化等方面展开讨论。每位学者报告时间约为六十分钟,与听众互动二十分钟。这次的暑期文化系列讲座是在疫情形势下做出的新尝试,在突破了场地的限制后,师生们在云端和中国文化相聚。
8月8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章伟文教授带来了“中国文化暑期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道德经>的智慧》。章教授结合大量生活中浅显易懂的实例为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了《道德经》在本体论哲学、政治哲学、境界与修养论以及认识论四个层面的智慧。章教授认为在本体论哲学层面,《道德经》的智慧可总结为“尊道贵德,道法自然”。“道”是万物生成的源头,也是世界万物之依据、本然。人类既要去自我中心,以物观物,又要回到“人”的角度,按照人类的目的去观察事物,发现规律。而万物按照其本性,处于最合适的位置上,则谓之“德”。而在政治哲学层面,《道德经》的智慧可总结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主观地妄为,应顺着事物内在发展规律和事物之性情而行动。具体到治国层面,既要“治大国若烹小鲜”,又要“小国寡民”。《道德经》在境界与修养论上告诫我们要上善若水,柔弱谦下。《道德经》认为理想的人格应像水一样做到能利万物而又不居功自傲,不与万物争利。而在认识论上,《道德经》的智慧可总结为“抱朴守真、静观玄览”。不同于康德的认识论,章教授认为《道德经》认识世界的方法是把“主观的我”搁置起来,“损之又损”,以达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境界。

章伟文教授:《〈道德经〉的智慧》
章教授的演讲引发了老师同学们的热烈讨论,有老师问及《道德经》的版本差异对经典解读的影响,章教授认为对《道德经》版本的考察是一个重要问题,牵涉到对其哲学智慧的理解。“老学”中就有对《道德经》演变历史和诠释历史的考察。有同学问《中庸》中的“道”和《道德经》的“道”有什么异同,章教授说两者的确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形而上的根本,而两者在价值取向、把握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有同学问创新需要打破规律,这与道家提倡的“顺应规律”是否有矛盾,章教授认为“创新”其实是一种“变”,并不是完全的“新”。还有同学提到当代大学生因学业、人际关系等感到焦虑,“道法自然”的观点是否能帮助大学生缓解焦虑,章教授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要以别人的价值来要求自己,应在社会上找到最合适展现自己的位置,活出自我。
8月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开讲“‘华夏中心论’的近代命运”。此次线上讲座,中心点聚焦在近代中国如何面对两种不同世界观融合的问题上。雷教授首先梳理了在“华夏中心论”的影响下,古代中国面对外来使节和国际交流时的表现,彼时由上至下大都秉持着“天朝上国”观念的中国人,将其他国家都看作是“蛮夷”,对外来的“奇技淫巧”如天体运行仪、火枪等器物没有看到它们背后体现的时代性变化,进而错失了主动融入近代世界的机会。而欧洲国家在17世纪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确立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此时的中国,自然无法意识到“外交”的意义。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不得不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但将外交事务交给地方官员的做法则为日后中国的发展埋下隐患,更加剧了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困顿和崎岖。经由这一番的讲解,在线师生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原因有了一定了解,结合现实,也有了更多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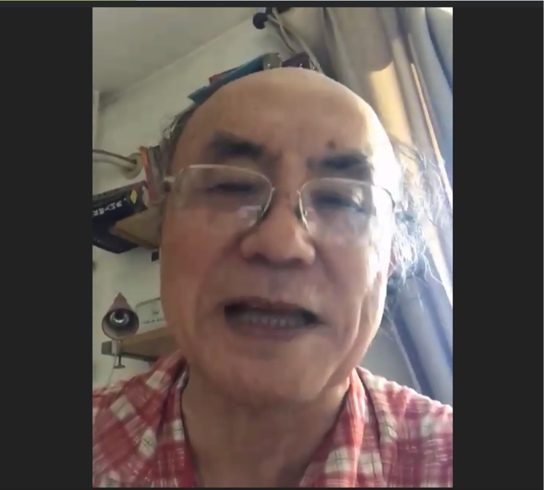
雷颐研究员:《“华夏中心论”的近代命运》
交流环节,师生都与雷教授有问答的互动。雷教授最后强调,学习历史不能只研究文本,虽然文本的阐释自有其一套理论的建构,但我们必须要看清现实,看看在文本的背后人们做了些什么。如此,我们回望过去,才可以尽可能“以史为镜”,鉴往知来。
当天下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传承人王芳老师在云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昆剧和苏剧艺术的赏析。讲座伊始,王芳老师先是围绕着“昆腔悠远,苏韵流芳”这一话题,详细讲解了昆剧和苏剧两种剧种在历史上的渊源,在艺术表现上的同与不同。而后在阐释为何昆剧被誉为“百戏之祖”时,王老师更是结合多年舞台经验,从“四功(唱、念、做、打)”和“五法(手、眼、身、法、步)”这些戏剧表演的基本技法方面一一进行了诠释。如在讲解“手法”之时,王老师从杜丽娘、武则天、李三娘三类不同人物角色出发,现场演绎了兰花指的多种手法,即如何通过身体形态表现不同人物的情感、性格特征、社会阶层等等。这种将阐述和表演融合一体的浸入式讲解方法,使听众也不禁隔着屏幕,跟随着王老师一步步进行学习和感受。王老师也谈到,艺术是来源于并高于生活的,戏剧演员要善于观察生活,使得舞台上的演绎真实可信,同时又要发挥一定想象力,在有限的空间内表现无限的故事,只有在各方面尽善尽美地塑造好一个角色,才能将这一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尽数展现给大众。

王芳老师:《昆剧苏剧艺术赏析》
在讲座的最后,有听众提出昆剧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的推广,通常是以大众影视文化为契机而引发关注,在昆剧的流传与发展中,案头之曲和场上之曲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现状。王老师首先肯定了现代的传播方式,认为这一传统艺术应从多方面渠道,借助多手段来让更多人了解其珍贵与可爱之处。同时,在昆剧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如《牡丹亭》、《长生殿》一类爱情戏曲,对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强,必将流芳百世。
8月11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红教授带来了《大诗人笔下的小人物——以唐诗为例》的讲座。王教授以杜甫在夔州时期写下的《信行远修水筒》一诗为引入,介绍了唐代诸位诗人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在杜甫之前,虽也有屈原、王褒、陶渊明等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仆人的例子,但大多只是作为主角的陪衬或调侃的对象,而杜甫在诗中则充满体恤和对仆人淳朴品性的赞美,其细腻的笔法和平视、欣赏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接着王教授也用高适、白居易等人对农民的态度与杜甫作了一个对比,进而谈到了诗仙李白笔下的小人物,如汪伦、宣城纪叟,是“生死歌哭、风华绝代”,而生性耿介的晚唐诗人罗隐写妓女云英,则同时体现了他的自嘲与嘲人、自卑与自信。最后王教授总结道,诗人们以这些弱者、小人物入诗,有关怀、有共情、有同理心,让更多的小人物在诗中看到自己,找到慰藉,汲取微弱却恒久的力量,而我们读唐代大诗人这些“不起眼”的诗作时,也更能深切地体会到文学是弱者生命中的光和热。

王红教授:《大诗人笔下的小人物——以唐诗为例》
在交流环节,王红教授也热情地回答了听众的各种问题,如有同学让王教授推荐一些适合入门者的诗词类书籍,王教授推荐了顾随先生和叶嘉莹先生的著作,但强调所有这些都比不上自己深刻而贴近的阅读体验,而且某些作品是需要年岁和阅历的,有时触景生情更能令人体会到诗中的情感,只看他人的转述终究是隔了一层。有人问到王教授如何评价梁启超把杜甫称为“情圣”的评价,王教授认为,杜甫的确是一个深情之人,在亲情、友情、爱情方面,都无愧于“情圣”之称。也有人提到,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天赋的人学写诗学不成李白,但学杜甫却能学成“小杜甫”,对此王老师表示,李白的诗是天才的发挥,没有拘束、没有法则,而且他身上有异族等多元文化的影响,的确是难学的,而杜甫的诗歌艺术能形成模式、形成规范,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同宇文所安所说,他的确为后来的很多人树立了规范。
8月12日上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彭国翔先生为师生做了“如何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心’人”的专题报告。彭教授首先厘清有“心”人的“心”最早在学术上可以追溯到孟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由此与动物、禽兽区别开来。彭教授接着指出恻隐之心其实就是一个本心,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用过这个词,后来王阳明将其真正发展成哲学概念,提出良知,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良心。在儒家看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做一个有心人首先要找回丢失的良心,同时就像镜子蒙尘要时时擦拭一样,在每一个场合都要历练自己,让自己的本心有觉悟的机会。讲到要如何做时,彭教授认为我们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通过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进而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培养自己的理性。最后彭教授还指出现代社会相对传统社会来说价值更加多元和相对,做一个有心人更不容易,也就显得更有必要。

彭国翔教授:《如何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心”人》
问答环节,有同学提问价值多元对现代人的积极意义有哪些,面对多元信息时又该提倡哪种做法?彭教授认为,就像美食的选择越来越多一样,价值多元是好事,可以哪种对胃口吃哪种,但是选择太多并且总是要自己选也会带来痛苦,因此要不断学习最终形成自己的理性价值,在理性思考后做出适合情况的个人选择。
8月13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乃龙教授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开讲,他说古人的梦想在今天通过屏幕信息技术成为现实。我们在云端的确就是“天涯若比邻”。随后开始了他的主题演讲:“《庄子》逍遥理论的现代价值”。他说到每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梦想就是要过好日子,而哲学家对好日子的定义和普通人是不同的。庄子的好日子就是“逍遥”。逍遥指的是高不高兴由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自在。接下来李教授通过“人为何不逍遥?”、“怎样才算逍遥?”“如何才能逍遥”三个方面来讲解庄子系统的逍遥理论。李教授说人在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范畴都不逍遥,因为自然人需要吃饭,并且只会走不会飞,最终一定会死;而作为社会人则因为要跟他人联系,那么他人的态度就会导致人的不自在,所以人不逍遥。在谈到逍遥的具体内涵时,李教授分别介绍了“彷徨”、“茫然”和“无为”三个重要的概念。他说,“彷徨”是指人形体上的随意的无目的的走动;“茫然”则是指心理上的没有欲望,不问是非,不追求名利,也就是朴;“无为”则是跟有为相对,指的是干任何事都是顺其自然的。所以庄子的逍遥理论是从形体到心理到行为的一套理论系统。最后达到无动于衷就是逍遥。最后李教授讲到若干途径来实现逍遥。其一是“无待”,待是依靠,无待就是没有依靠。虽然人们常说“有恃无恐”,也就是说无恐是建立在有恃之上的,然而就庄子的理论看来,有恃无恐不如无恃无恐。因为凡是依靠都有限制,所以有待不逍遥,无待才逍遥。其二是“无己”,无己就是忘己,忘掉自己的尊严、面子、得失等。因为人们常认为天地之间自己最重,所谓“一己之私”,所以要把自己的私忘掉。其三是“无功”,庄子说的无功,指的是人不应该主动的、刻意的、有目标的去立功,而是应该自然而然的立功,他反对为自己而居功的。庄子说最好的立功就是天地一样,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老天大地把所有的美都制造出来,但是从来没有表功说这些是我做的,所以是有功而不居功。其四是“无名”,名声是人的第二张脸,就是要面子,面子是别人给的,无名不是什么事都不干,而是干了好事不要去追求名声,因为一味的追求会给人带来不逍遥。最后李教授总结道,庄子提出的“逍遥”其实是针对人性的弱点来设置的,人类因为弱小所以必须要寻找依靠,人类对名利都特别争抢,而且希望有好的结果,特别在意面子等等。他的核心是“自在”,因此庄子的逍遥理论具有永恒的价值。

李乃龙教授:《〈庄子〉逍遥理论的现代价值》
在提问环节,有同学问李教授,庄子本人是否到了逍遥的境界?李教授回答说,庄子自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说都得到了逍遥,但是其他人都没有实现逍遥。从庄子的经历看,他是贵族沦落为平民,身份的落差让庄子带有鄙世的眼光。庄子的思想深度又极高,是一个隐士的形象。他开始是被迫的被动的逍遥,后来是主动的逍遥,不能回归也不再屑于回归。因为他已经看透了。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吸收庄子理论的价值,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具有当代价值。
8月14日下午,UIC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的董铁柱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越王勾践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分享。董老师说到自己与著名历史学家柯文交流的经历。他说,勾践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位历史人物,但对于柯文,这样一位著名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他却不知道“卧薪尝胆”的意思,不知道勾践是谁。所以柯文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对本国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由此展开了演讲和自己的思考。董老师首先大致介绍了越王勾践的故事。从基本内容上说,读者可以读出耻辱、复仇、复兴、坚持等等内涵,所以勾践故事的意义具有多元性,正面而论是卧薪尝胆、信任大臣等;负面则是阴谋诡计和兔死狗烹。那么当我们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会发现受辱、复兴的主题。所以越王勾践的故事在20世纪被不断传扬。正是因为勾践的故事是具有“弹性”的,因此我们对于勾践的理解、范蠡文种的理解、西施、夫差等等人物的理解都可以不同。接着,董老师给大家梳理了20世纪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勾践故事的差异和变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流行的故事来看,当时的人们都希望有英雄出现,所以此时勾践的故事受到重视。柯文分析其中的原因时,指出因为人们善于遗忘,而勾践故事的意义在于勾践始终铭记着耻辱。所以此时勾践的形象是和复仇、不忘耻辱相联的。之后,从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到1940年代末的中国内战,勾践故事的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宣传这一故事的渠道种类繁多。其次,不少关于这一故事的出版物一版再版,这意味着它有着广泛的读者。第三,这些出版物通常都有官方的许可证明。第四,极力将勾践的故事融入在平民普及教育读物里,也将其纳入了各个级别的学校课程之中。同时,勾践故事在教育界、媒体界得到广泛宣传。董老师介绍了熊佛西《卧薪尝胆》、陈大悲《西施》、丰子恺《九一八之夜》等当时的名篇,指出对于勾践故事不同的切入点和评价,从而总结出这一时期勾践故事的三个特点。首先,勾践被描述成为了一雪前耻而甘愿遭受生活的贫困和个人的羞辱,与此同时,他耐心准备,伺机复仇。其次,勾践和夫差两人的所作所为表明,如果想要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话,纳谏对于君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后,在所有的例子中,勾践故事都以越国灭吴和勾践圆满复仇为结局。在1950年之后,董老师又介绍了陈文泉、谭峙军以及曹禺、萧军等人对勾践故事进行的再创作。通过这些戏剧资料的梳理,董老师说任何一个历史的故事都是可以灵活诠释的,所以就涉及到历史和小说的真实性可靠性的问题。既然这些故事都是可以被灵活运用,那么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不是去质疑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写,他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希望通过越王勾践的例子给大家一些启发。

董铁柱老师:《越王勾践与二十世纪中国》
8月15日上午,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的杨志翔老师与大家分享了 “胡适、杜威与白话文运动:从儒学传统到实验主义”。杨老师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了胡适先生的基本情况,然后解释杜威的“实验主义”,最后讲到了胡适和杜威的关系。杨老师在介绍胡适时,强调他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倡导者地位。同时,胡适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代言人。胡适当年利用庚子赔款赴美求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而杜威正是他的老师,除了胡适之外,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中国留学生还有陶行知先生、蒋梦麟先生,张伯苓先生等。这些人物在中国文教界都是举足轻重的,其后的业绩也都相当辉煌,为中国的文教事业留下了长远的回响。谈到杜威,杨老师说杜威思想代表着西方哲学的美国化,是整个哲学话语体系跟美国的现实情况结合后产生的哲学。因此杜威哲学是一种提倡社群中保持人性的哲学,并且杜威主张用科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在介绍杜威的生平时,杨老师着重介绍了1919-1921年的杜威访华。此时的杜威来到刚刚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当他看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他很兴奋,所以在中国两年2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两百多场演讲,涉及到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在杜威眼里,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渗透着这种启迪民智的情怀。最后一个部分杨老师介绍了胡适和杜威之间的联系。胡适是一个新派人物,他的思想发展主要受到父辈家庭的影响,同时从中国的传统经典中受到启发。所以胡适更注重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注意教育的教化作用,这是胡适走向杜威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则是乾嘉朴学的影响。胡适有考据的学术习惯,而他认为考据学的思维方式和杜威的思维方式很通融,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原因之三是和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相关。经世致用主张学的东西要有用于当时,落实到胡适当时所处的时代,就是要求他们去找寻让民族起死回生的方法。怀揣着这样的目的和情怀,胡适走向美国、走向了和中华传统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胡适投到杜威门下。演讲的最后,杨老师用胡适晚年很喜欢的一首宋诗结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指出胡适一生都尝试将实验主义运用在教育、文化、文学中,因为时代的原因,他的业绩在中国大陆被埋没了,但他是一位把做人和做学问结合在一起,来努力的尽心尽力的打拼,力争上游的人。

杨志翔老师:《胡适、杜威与白话文运动:从儒学传统到实验主义》
第九场讲座是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的陈颢哲老师的《〈史记〉: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一本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今天陈老师的分享主要围绕“司马迁到底想从史记中告诉我们什么”展开,从而回应一个常见的问题“读历史,到底要读什么?”陈老师先简要介绍了《史记》和司马迁的基本情况。他说在文学上,司马迁是非常受到尊敬的,他的文笔非常好,但是《史记》中还留有很多不大好看的篇章,陈老师今天特意选择一些,希望借此说明应该怎样去读《史记》,能让同学们学着用司马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在史学上,司马迁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系统批评司马迁的有唐人刘知几,他认为《史记》没有继承孔子《春秋》的精神,没有具备善恶标准以及是非评价。从体例上说,纪传体的设计让史料非常分散,不容易获得完整的历史信息。并且司马迁虽然自创体例,但又常常不合规矩来。例如将陈涉、孔子都列入世家中。最后司马迁将很多历史事件的原因都归咎到天意上,显得虚无缥缈。基于这些指摘,陈老师解释道,司马迁的确是创造出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种体例,作为正史的开创者,因此是“史家之绝唱”。那么对于司马迁来说,他想要写的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从《太史公自序》以及《报任少卿书》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并不是站在汉王朝的立场去撰写历史,更不是利用历史的撰写来服务皇家。他所主张的是恢弘视野的历史观,也就是原初的《春秋》精神,透过历史来对一切的人事物进行评价与批判。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写一本能够解释历史事件的书,不是要告诉人们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想说明历史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是如何慢慢转变、发展,最后影响到他生活的时代。随后,陈老师用一些具体的篇目来详细解释了“究天人之际”的真正内涵。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史家能做的就是区分天和人的界限,哪些是属于天意,哪些是属于人事,天意最终决定了结果,但关注人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在意过程。由此也显示出史家的重大责任。就是不以结果论,而是把值得记录下来的人生书写出来。“通古今之变”则是司马迁认为的史家和历史的关系,他意识到自己写下的东西是他自己在观察历史的动向、人物和事件相互作用后归纳出的一套历史解释。也就是“究天人之际”后,“通古今之变”最终写成一本名为《史记》的“一家之言”。当获知了司马迁撰史的目的后,陈老师接着挖掘了一些在《史记》中表现出的司马迁独特价值观。例如他写《陈涉世家》、《孔子世家》、《吕太后本纪》,证明司马迁认为历史的重心不一定是随着所谓的名义上的天子皇帝运行。从具体的篇章描写中,亦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同的历史情况解读。例如司马迁对吕太后的评价。所有这些都在告诉读者,历史的解读不能只有一个视角。总之,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想办法对历史提出解释,去试图找出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但同时司马迁也坦诚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有解释。当然司马迁也谦逊的说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所以陈老师说,我们可以从《史记》中读到的就是:面对历史,没有正确答案,只有很细心很细腻的去推敲,才能在历史中学到一些真正的知识和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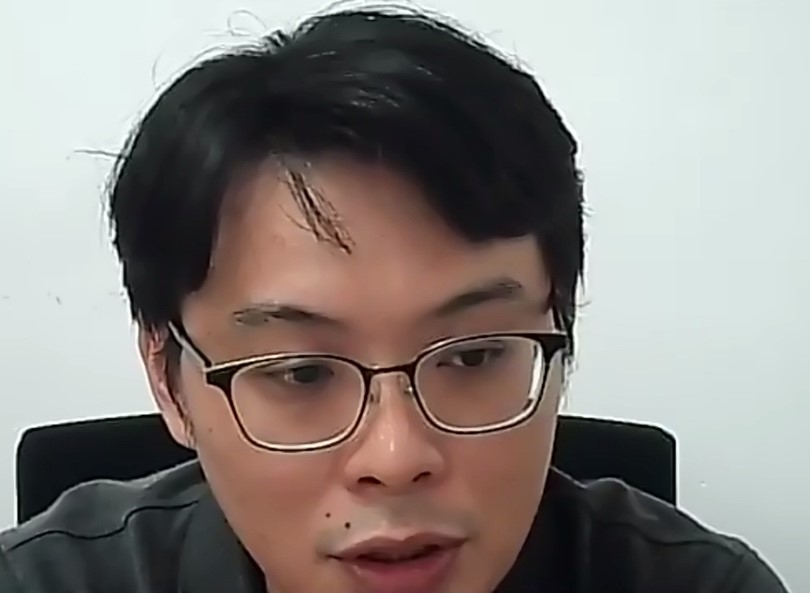
陈颢哲老师:《〈史记〉:无韵之离骚》
8月17日,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伍鸿宇老师带来了“中国文化暑期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天下与万国: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再思考。伍老师坦言,选择这个比较旧的题目是着眼于UIC的国际化特色,同时我们也对传统文化有一份温情和敬意,UIC的学生需要去了解国际化的动力在哪里,以及我们怎么更好的走向世界。通过这次讲座,伍老师介绍了近代历史上,传统中国天下观面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所经历的曲折历程。通过“番妇入华”的历史事件,了解天下观的夷夏有别。通过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发现近代世界知识如何进入中国人视野。通过马葛尔尼、阿美士德和律劳卑事件,回顾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碰撞过程。同时,伍老师也对传统天下观的性质、特点和发展变化进行了再思考:天下观是中国独有的吗?它是一个稳定的封闭系统吗?古代中国缺少世界知识吗?为什么有丰富的世界知识却形成不了新的世界图像?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是近代才产生的吗?“天下观”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吗?等等。伍老师认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的确占据历史的优势地位,但是民族国家观念也容易导致战争和奴役。而传统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基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创造出的价值体系。通过地图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5世纪中国的天下观念就建构在世界各国地理知识上。这是那个时代全球化的结果。可见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世界带来启发,我们需要走出传统的天下观,打破心中的固念和偏见,抱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信念,为世界提供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观念。最后,在讨论环节,大家进一步探讨了文明的价值判断,思想文化的立场等问题。

伍鸿宇老师:《天下与万国: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再思考》
至此,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化暑期系列讲座”全部结束。伍老师感谢六位校外专家学者和三位中心同事的支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讲座,也感谢同学们和UIC亲友团的积极参与,共同讨论,使得这次特别的在线讲座取得了和线下讲座一样的效果。他最后感谢中心同事们的付出,为大家营造了非常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希望以后中国语言文化中心还有机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学术活动。
